风力发电技术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风能,风力机风场多数建立在风能资源比较丰富的区域,其中也有些是地震活跃地带[1].运行中的风力机不仅受到空气动力载荷的作用,也可能面临突发地震的冲击[2].风力机结构属于质量较大而且高耸的结构,当风力机受到气动与地震等多种载荷同时作用时,风力机的结构安全和稳定运行都难以得到保证[3-4].研究表明,相对于竖向地震载荷,水平地震载荷是影响风力机可靠性运行的主要因素.由于地震波传播方向的不确定性,研究不同水平地震方向对风力机响应的影响对保证风电机组可靠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上开展风力机结构地震响应研究的时间还不长,研究者们利用地震反应谱法和时域法针对不同的机型开展了研究工作[1].Zhao等[5]建立了风力机塔架的多体动力学模型,通过Wolf方法[6]简化土![]() 构耦合为不同方向的多个弹簧振子组合,计算了地震发生时塔顶位移时域响应.目前我国在此方面开展的研究,尤其是对整机进行系统的动力学研究的报道并不多见.曹必锋等[7]采用梁单元对水平轴风力机塔架进行有限元建模,把地基假设为刚性,侧重分析地震对风力机塔架动力响应的影响,但没有考虑土
构耦合为不同方向的多个弹簧振子组合,计算了地震发生时塔顶位移时域响应.目前我国在此方面开展的研究,尤其是对整机进行系统的动力学研究的报道并不多见.曹必锋等[7]采用梁单元对水平轴风力机塔架进行有限元建模,把地基假设为刚性,侧重分析地震对风力机塔架动力响应的影响,但没有考虑土![]() 构耦合和水平地震方向对风力机响应的影响;何玉林等[8]应用基于多柔体动力学的联合仿真技术对地震作用下的风电机组振动响应进行了研究,同样忽略了土
构耦合和水平地震方向对风力机响应的影响;何玉林等[8]应用基于多柔体动力学的联合仿真技术对地震作用下的风电机组振动响应进行了研究,同样忽略了土![]() 构耦合作用和地震波传播方向的影响.
构耦合作用和地震波传播方向的影响.
考虑运行中风力机同时受空气动力载荷、重力、惯性力等机械载荷以及地震波冲击载荷的耦合作用,本文基于多体系统动力学理论,利用超级单元模型建立了自由度较少的风力机整机动力学模型,模型中引入土和结构相互作用的Wolf土![]() 构耦合模型[6]模拟地震波对机组的冲击.根据国家抗震设计标准生成了正向和侧向两个水平方向的地震加速度时程,利用时程分析法仿真计算了风力机联合风载荷、机械载荷以及两个水平地震作用下的响应,考察不同地震波传播方向对机组响应的影响.
构耦合模型[6]模拟地震波对机组的冲击.根据国家抗震设计标准生成了正向和侧向两个水平方向的地震加速度时程,利用时程分析法仿真计算了风力机联合风载荷、机械载荷以及两个水平地震作用下的响应,考察不同地震波传播方向对机组响应的影响.
模拟土地和结构相互作用的方法有连续介质模型法和有限元法,但模型过于复杂或者耗时过长,并不便于实际应用.利用具有一定刚度K和阻尼C的弹簧振子表示土![]() 构耦合(solid structural interaction,SSI)是一种简单可行的方法,在研究中得到认可和应用[6],其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
构耦合(solid structural interaction,SSI)是一种简单可行的方法,在研究中得到认可和应用[6],其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
根据土体性质和基础尺寸确定弹簧刚度和阻尼系数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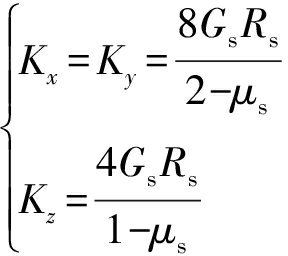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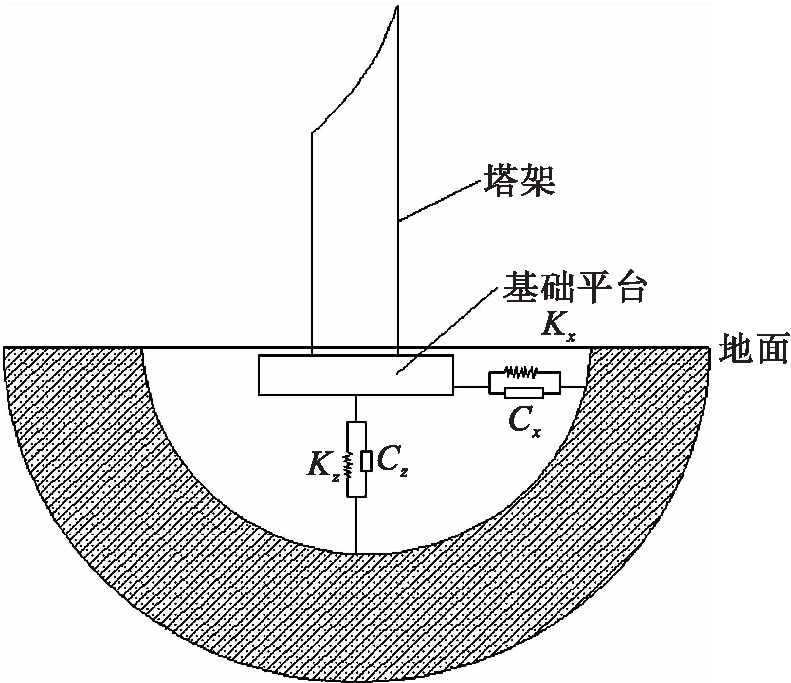
图1 土![]() 构耦合模型
构耦合模型
Fig.1 SSI mod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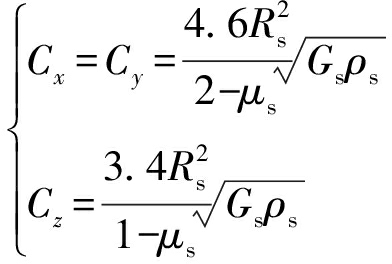
(2)
式中:下标x、y、z为方向,x为来流风速的方向,z为垂直方向;Gs、μs和ρs分别为土壤的切变模量、泊松比和密度,本文根据实际情况取值分别为55 MPa、0.333和2 700 kg/m3;Rs为基础平台的半径[7].
抗震设计用的加速度反应谱在我国抗震设计规范中称为地震影响系数α曲线,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αmax决定于烈度,谱形状决定于场地相关反应谱.风电高塔系统属于高耸结构,水平方向和竖向地震载荷都不能忽略.本文依据国内抗震设计标准GB50011-2010模拟生成了水平和竖向两个方向的加速度时程,地震载荷以加速度时程的形式作用在基础平台.图2为地震水平方向地震影响系数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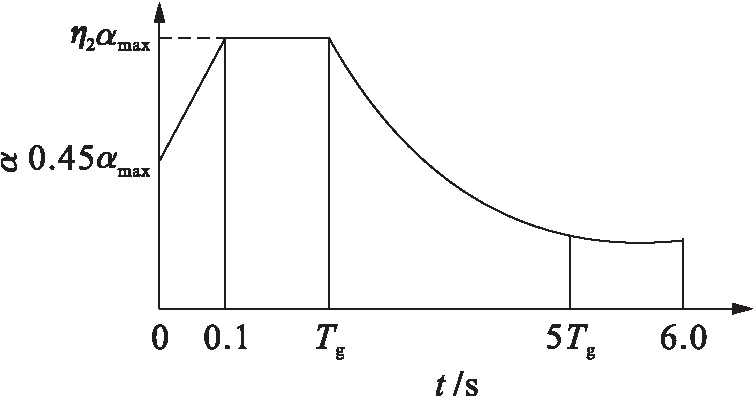
图2 地震影响系数曲线
Fig.2 Seismic impact coefficient curve
地震水平向影响系数表达式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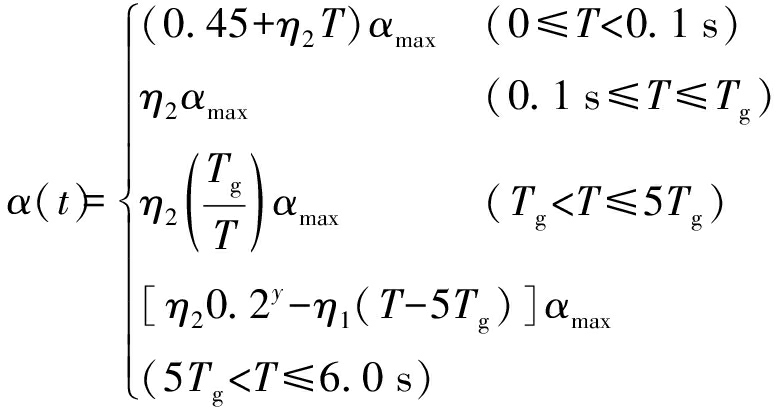
(3)
式中:α(t)为地震影响系数;αmax为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Tg为特征周期;T为结构自振周期,取1 s;y为衰减系数;η1为直线下降段斜率调整系数;η2为阻尼调整系数.当结构阻尼比不等于0.05时,曲线衰减系数y、η1和η2表达式为
y=0.9+(0.05-ζ)/(0.3+6ζ)
(4)
η1=0.02+(0.05-ζ)/(4+32ζ)
(5)
η2=1+(0.05-ζ)/(0.08+1.6ζ)
(6)
式中,ζ为阻尼比.按照当地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和特征周期,对目标加速度反应谱进行模拟,可生成水平向地震加速度时程.本文仿真分析设置该风力机抗震烈度为9度,地震影响最大系数为0.4g(g为重力加速度),特征周期为0.45 s,阻尼比为0.02,地震加速度发生时间为仿真的第10 s,总仿真时间为40 s,目标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和生成的水平向地震加速度时程如图3、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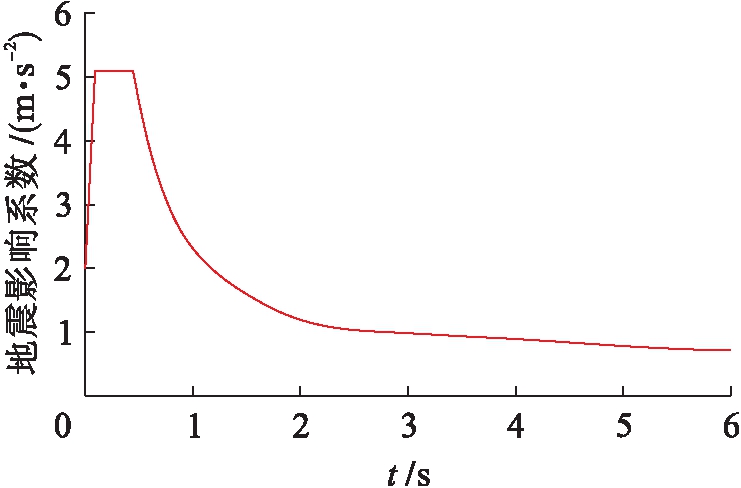
图3 目标地震影响系数曲线
Fig.3 Target seismic impact coefficient cur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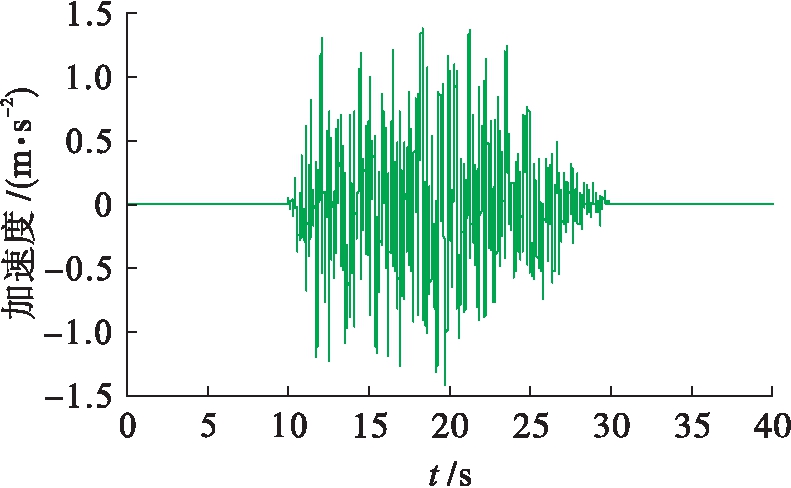
图4 地震加速度时程
Fig.4 Seismic acceleration time-history
在地震作用下的风力机还受到气动载荷、重力、惯性力等载荷作用,运行机组各部件在这种复杂的载荷工况下会产生复杂的振动和弹性变形,采用多体系统动力学理论建立机组的地震![]() 风
风![]() 弹性耦合动力学模型是可行且符合机组实际动力特性[9].
弹性耦合动力学模型是可行且符合机组实际动力特性[9].
计算风力机叶片气动载荷的方法有很多,如叶素动量理论(BEM)、涡流理论、动态失速模型(BL)以及计算流体力学(CFD)等.其中叶素动量理论(是叶素和动量理论的耦合)在风力机气动载荷分析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和认可,本文也采用这种模型进行叶片气动载荷分析[10].
风力机由相对轮毂转动的风轮、轮毂、机舱、塔架和基础平台等组成,各部分间存在相对运动,且机组工作时,各部分的运动与变形各不相同.采用刚柔混合多体模型建立风力机动力学模型[11],得到风力机多体模型后,可以根据多体动力学理论建立系统动力学方程,即
(7)
式中:Z为广义质量矩阵;z为广义力阵,反映了地震载荷、气动力、重力和惯性力的影响;![]() 为广义加速度;Øq为约束方程的雅克比矩阵;λ为拉格朗日乘子阵.该方程组为微分
为广义加速度;Øq为约束方程的雅克比矩阵;λ为拉格朗日乘子阵.该方程组为微分![]() 代数方程组,先利用数值方法求得
代数方程组,先利用数值方法求得![]() 然后数值积分求解广义速度
然后数值积分求解广义速度![]() 和广义位移q.动力学仿真流程图如图5所示,模型具体的建立和数值求解方法可参阅文献[10].
和广义位移q.动力学仿真流程图如图5所示,模型具体的建立和数值求解方法可参阅文献[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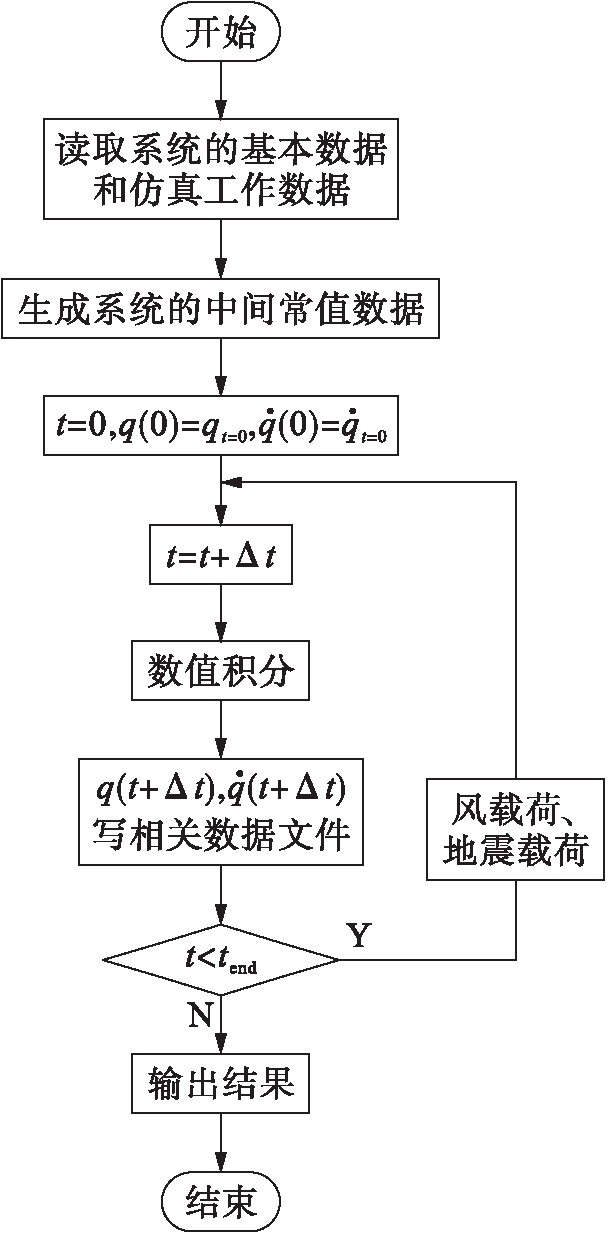
图5 动力学仿真流程图
Fig.5 Flow chart of dynamics simulation
以美国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开发的5 MW变速变桨距控制风力机组为对象进行分析,该机组性能参数可参阅文献[10].利用超级单元的离散方法,将叶片离散成4个超级单元,一共13个刚体.因为主轴会产生扭转,故将其分成两个刚体,用旋转铰连接.由于轮毂与主轴第一个刚体连接且无相对位移,可以当成一个刚体,机舱也作为一个刚体,机舱与塔架用球铰连接,塔架第一个刚体和基础平台刚性连接,整个风力机被分成55个刚体,91个自由度,建立的整机混合多体模型如图6所示.在额定风速11.4 m/s的工况下,对风力机分别输入两个水平地震方向(平行于来流方向的正向和垂直于来流方向的侧向),根据风力机的动力学响应结果分析不同水平地震方向对风力机振动变形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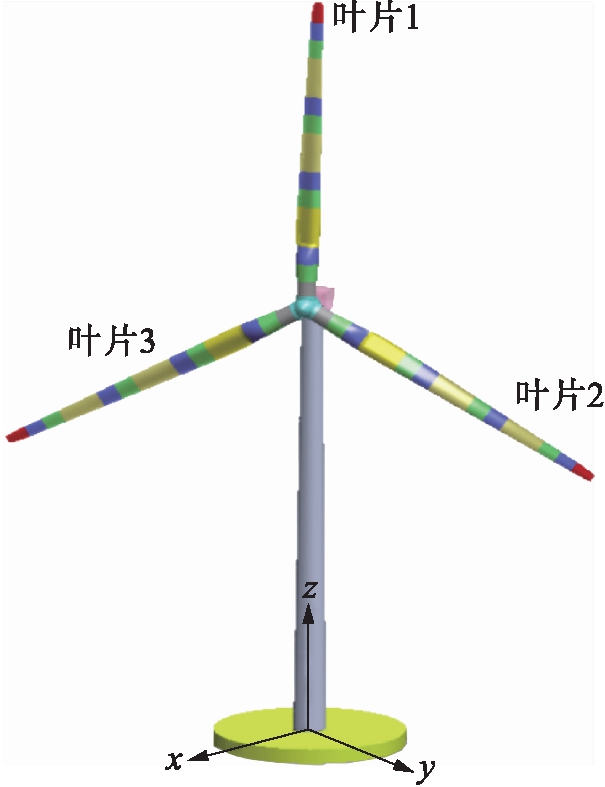
图6 整机坐标示意图
Fig.6 Schematic coordinate of whole machine
机舱加速度变化是反应塔尖振动情况的特征响应之一,图7、8分别为机舱两个水平方向加速度(即x、y方向)随时间的变化曲线.从机舱两个水平方向的加速度变化图可以看出,正向地震主要影响机舱x方向的加速度,而侧向地震主要影响机舱y方向的加速度,响应结果和地震方向一致.
叶片叶尖处是振动变形最明显的位置,图9为第三个叶片叶尖处挥舞方向振动变形加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图10为第三个叶片叶尖处摆振方向振动变形加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由叶尖振动变形加速度随时间的变化图可以看出,正向地震主要影响叶片挥舞方向的振动变形,且和模拟生成的地震加速度时程趋势一致.侧向地震对叶片两个方向的振动变形都有明显影响,相比于正向地震,衰减速度要慢很多.在叶片挥舞方向上,正向地震要比侧向地震影响程度大,最大加速度在第13.8 s达到了19.29 m/s2,比在没有受到地震作用下大12 m/s2,但在30 s后侧向地震明显要比正向地震影响显著.在叶片摆振方向上,侧向地震比正向地震的影响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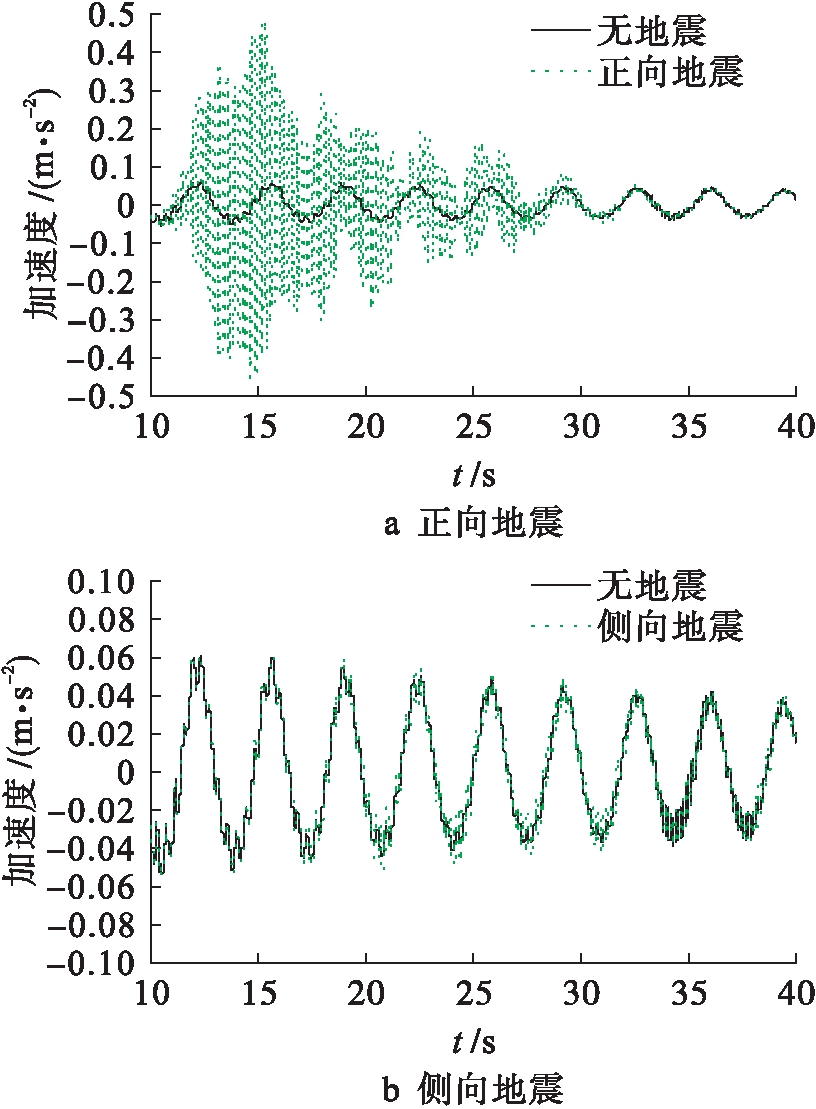
图7 机舱x方向加速度随时间的变化图
Fig.7 Change of acceleration with time in x direction of cab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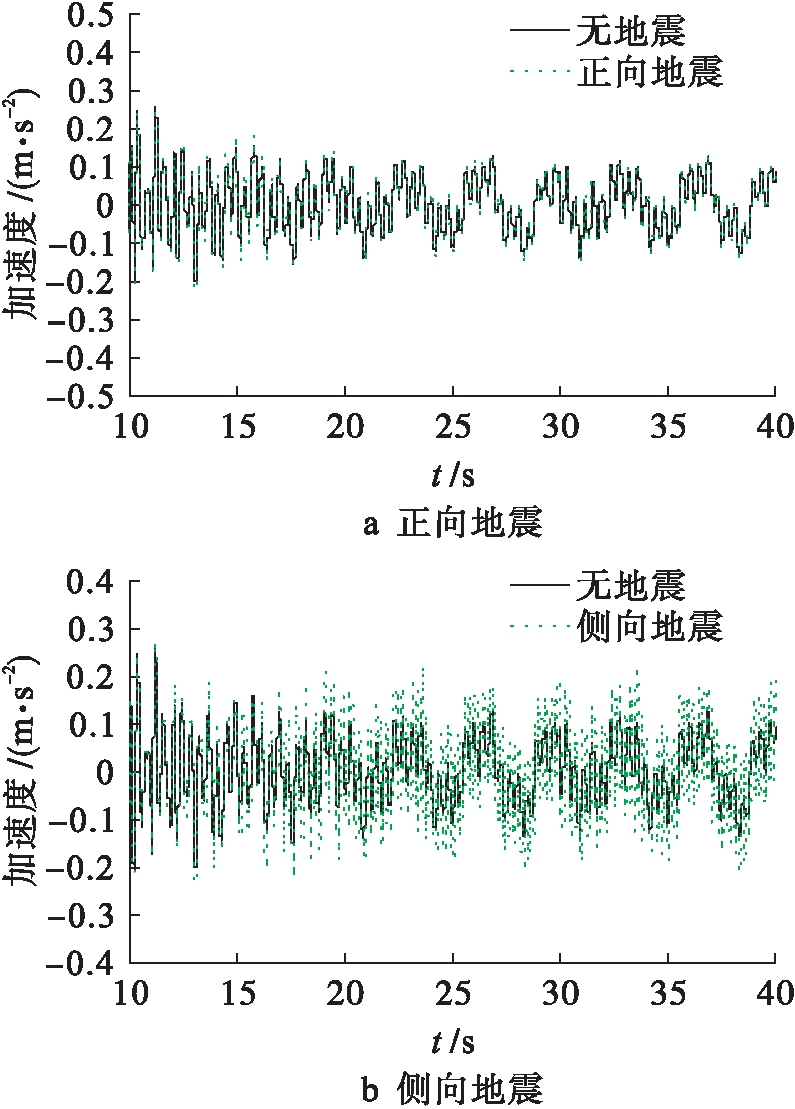
图8 机舱y方向加速度随时间的变化图
Fig.8 Change of acceleration with time in y direction of cab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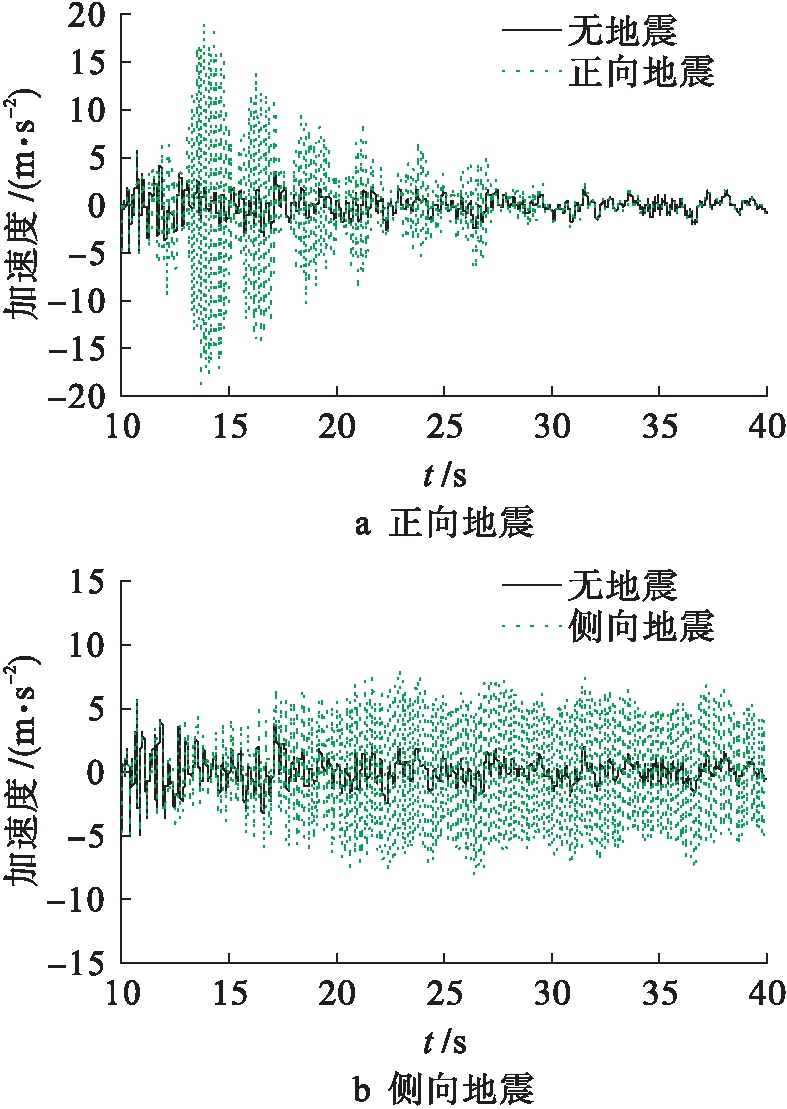
图9 叶尖挥舞方向振动变形加速度
Fig.9 Flapwise vibration deformation acceleration of blade ti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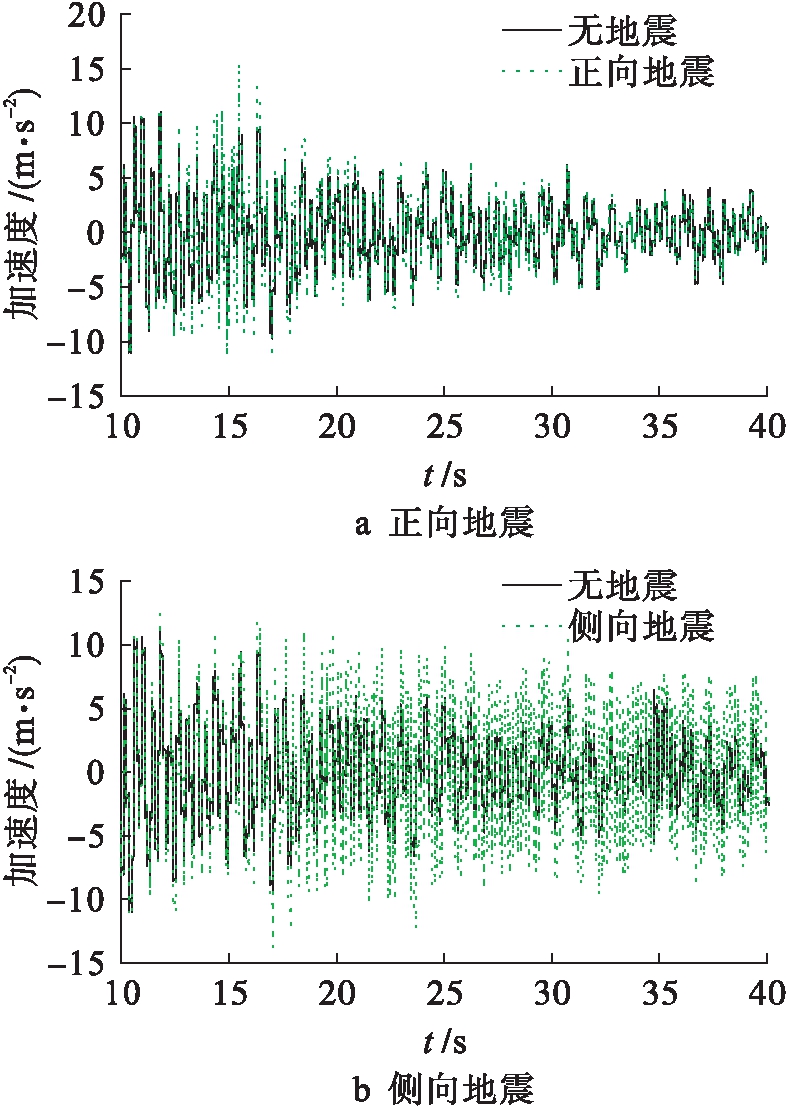
图10 叶尖摆振方向振动变形加速度
Fig.10 Edgewise vibration deformation acceleration of blade tip
叶片在叶根处承受着较大的挥舞力矩和摆振力矩,是风力机叶片结构设计的关键点,故叶根力矩在地震作用下产生的变化对叶片抗震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地震作用在基底,塔基受到的俯仰和横摇力矩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叶根挥舞与摆振力矩随时间的响应曲线如图11、12所示,由图11、12可以看出,风力机受到正向地震时,叶根挥舞力矩在6.7~8.1 MN·m之间变化,最大值比没有受到地震作用时要大1.1×105 N·m;相对于叶根挥舞力矩,叶根摆振力矩在正向地震时没有明显变化.当风力机受到侧向地震时,叶根挥舞力矩和摆振力矩都有明显波动,但叶根挥舞力矩变化要比摆振方向力矩变化明显.叶根摆振力矩在-5.5~2 MN·m之间波动,最大值比没有受到地震作用时要大8×105 N·m.依据叶根挥舞力矩和叶根摆振力矩的响应曲线可以看出,正向地震对叶根挥舞力矩影响尤为明显,侧向地震则主要影响摆振方向叶根处力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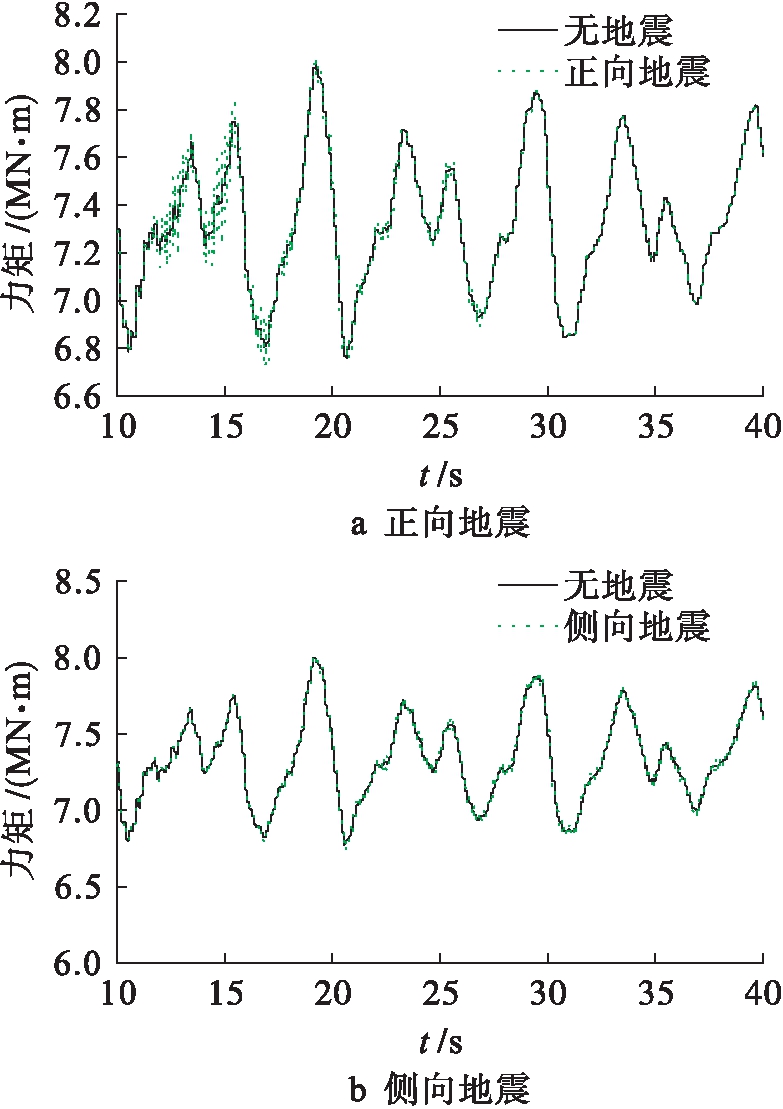
图11 叶根挥舞力矩
Fig.11 Flapwise moments of blade root
塔基的俯仰力矩和横摇力矩如图13、14所示,由图13、14可以看出,风力机受到正向地震作用时塔基的俯仰力矩变化比横摇力矩的要明显,此时塔基的俯仰力矩在-5×107~1.7×108 N·m之间波动,力矩最大值比在没有受到地震作用时大7×107 N·m.相反,风力机受到侧向地震作用时塔基的横摇力矩变化比俯仰力矩的要明显,此时塔基的横摇力矩在-2.2×107~2.2×107 N·m之间变化,力矩最大值比在没有受到地震作用时大1.1×107 N·m.从塔基的力矩响应可以看出,正向地震主要影响塔基的俯仰力矩,侧向地震主要影响塔基的横摇力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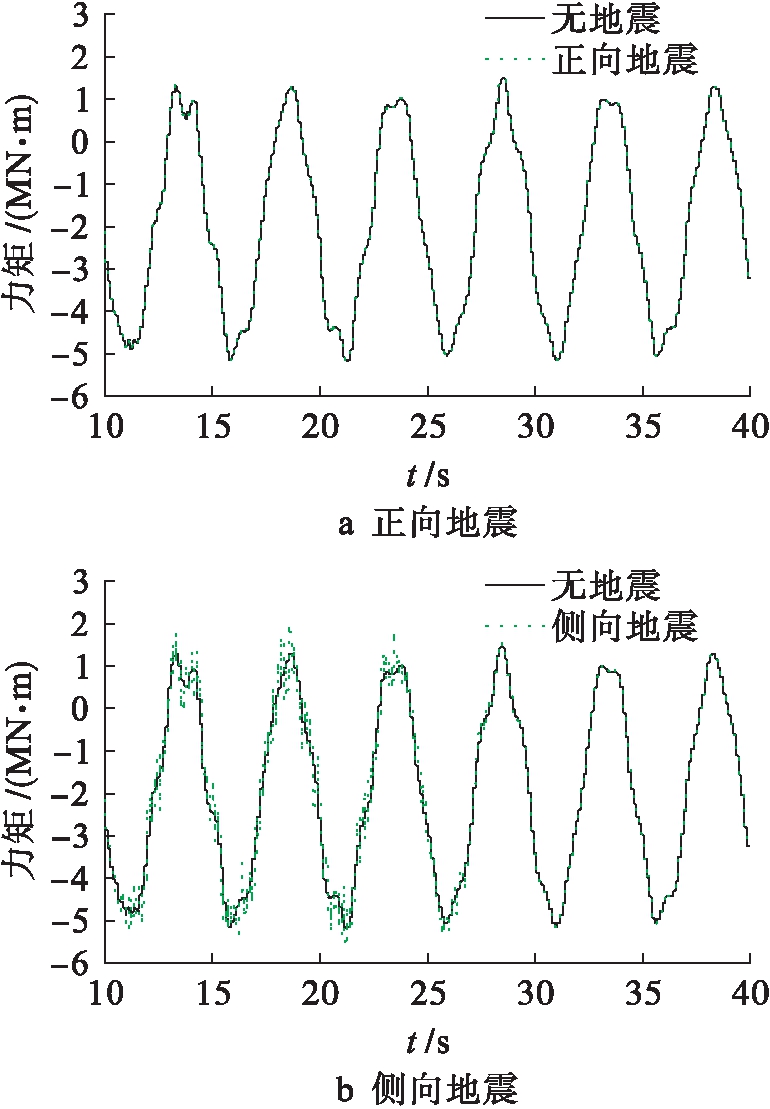
图12 叶根摆振力矩
Fig.12 Edgewise moments of blade ro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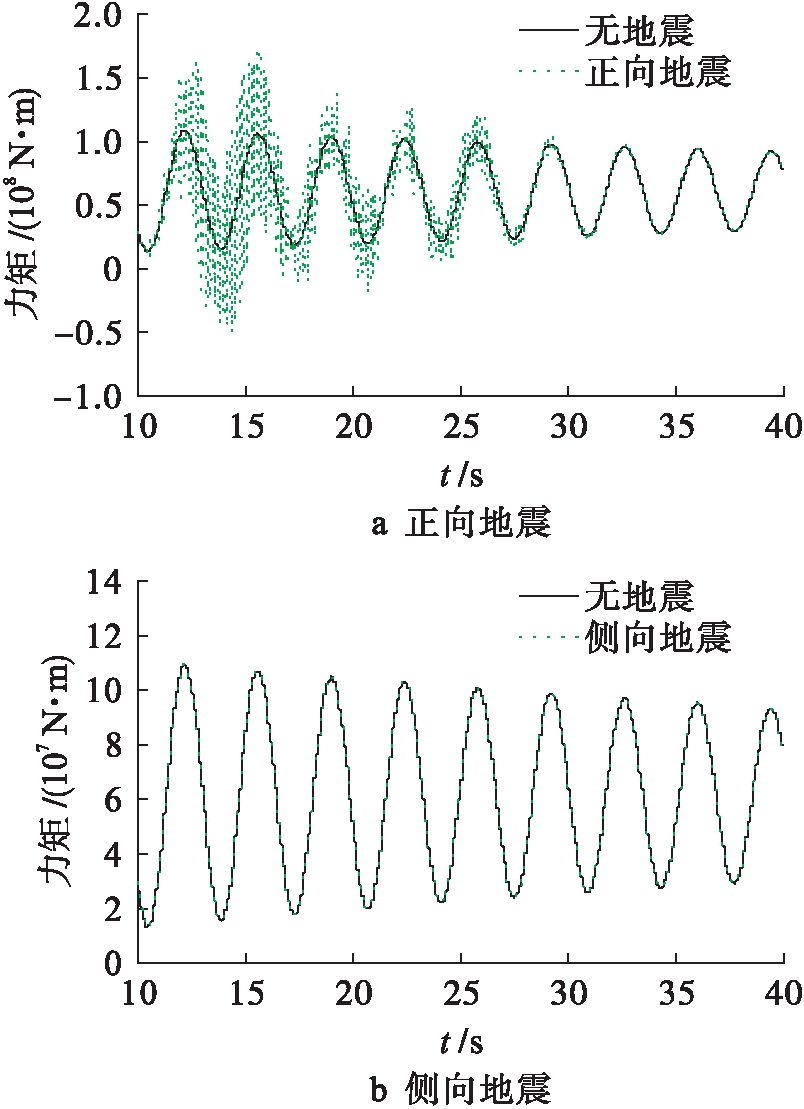
图13 塔基俯仰力矩
Fig.13 Pitching moment of tower foundation
通过建立风力机机组多体动力学模型,并在其中引入土![]() 构耦合作用,实现了风力机整机在地震作用下的动力响应数值分析和模拟.通过对比正向和侧向两个水平地震方向对风力机的响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构耦合作用,实现了风力机整机在地震作用下的动力响应数值分析和模拟.通过对比正向和侧向两个水平地震方向对风力机的响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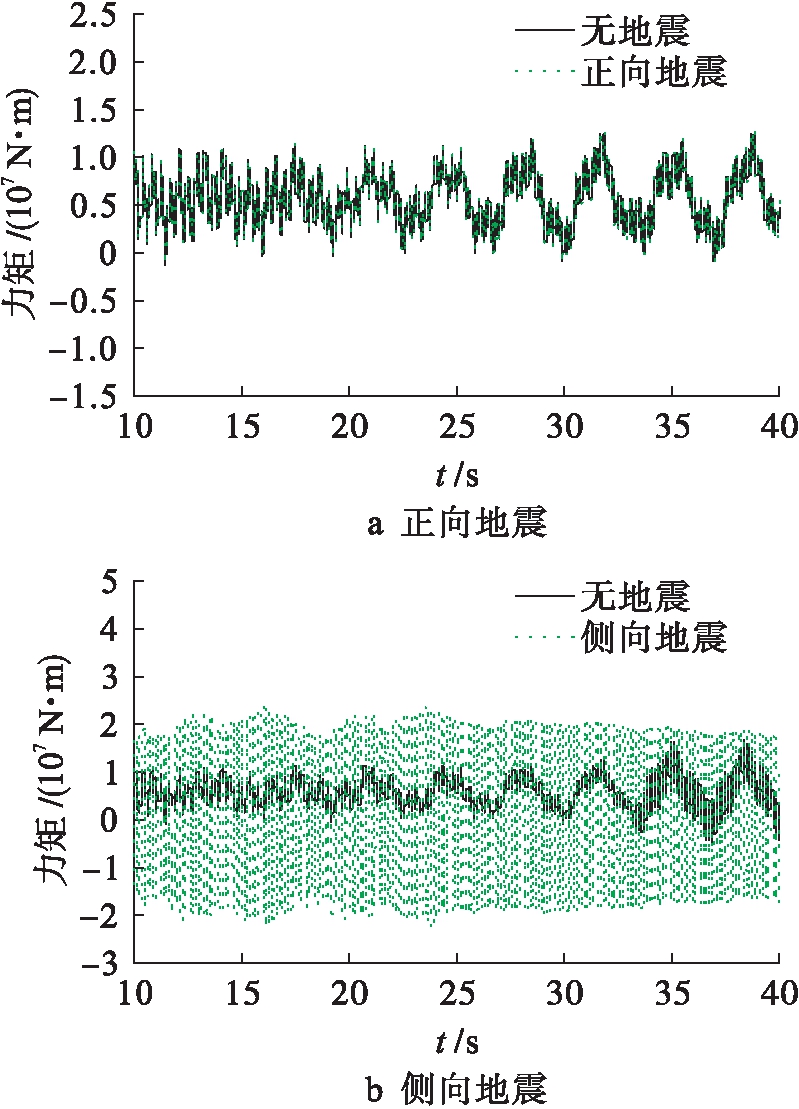
图14 塔基横摇力矩
Fig.14 Rolling moment of tower foundation
1) 正向地震主要影响叶尖挥舞方向振动变形,其影响程度比侧向地震要更剧烈,侧向地震对叶片挥舞方向和摆振方向的振动变形都有影响,摆振方向上,侧向地震影响更明显.在叶根力矩方面,正向地震主要影响叶根挥舞力矩,最大值比原来增加了50.34%,侧向地震主要影响叶根摆振力矩,最大值比原来增加了66.67%.
2) 在地震作用下机舱的水平方向加速度和塔基的力矩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机舱的两个水平方向加速度响应和地震方向保持一致,正向地震主要影响塔基的俯仰力矩,最大值比原来增加了63.62%,侧向地震主要影响塔基的横摇力矩,最大值比原来增加了98.23%.
3) 研究工作对于风力机组的抗震设计与保障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特别是考虑地震波不同的传播方向对运行中机组的冲击具有参考价值.
[1] 杨阳,李春,缪维跑,等.湍流风场与地震激励联合作用下的风力机结构动力学响应 [J].振动与冲击,2015,34(21):136-143.
(YANG Yang,LI Chun,MIAO Wei-pao,et al.Structural dynamic responses of a wind turbine under turbulent wind combined with seismic motion [J].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Shock,2015,34(21):136-143.)
[2] 范洪军,金全洲,潘文欢,等.高阶振型对风力机塔架地震反应的影响分析 [J].太阳能学报,2013,34(3):513-525.
(FAN Hong-jun,JIN Quan-zhou,PAN Wen-huan,et al.Contributions of higher modes in seismic response analysis of wind turbine towers.[J].Acta Energiae Solaris Sinica,2013,34(3):513-525.)
[3] Asareh M A,Schonberg W,Volz J.Effects of seismic and aerodynamic load interaction on structural dyna-mic response of multi-megawatt utility scale horizontal axis wind turbines [J].Renewable Energy,2016,86:49-58.
[4] 练继建,燕翔,王海军.新型重力式海上风力机基础结构动力特性分析 [J].太阳能学报,2016,37(6):1624-1630.
(LIAN Ji-jian,YAN Xiang,WANG Hai-jun.Dynamic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newtype gravity infrastructure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 [J].Acta Energiae Solaris Sinica,2016,37(6):1624-1630.)
[5] Zhao X,Maisser P.Seismic response analysis of wind turbine towers including soil-structure interaction [J].Journal of Multi-body Dynamics,2006,220(1):53-61.
[6] Wolf J P.Spring-dashpot-mass models for foundation vibrations [J].Earthquake Engineering & Structural Dynamics,1997,26(9):931-949.
[7] 曹必锋,衣传宝.风力机塔架在风![]() 地震作用下的动力响应 [J].噪声与振动控制,2014,34(4):205-208.
地震作用下的动力响应 [J].噪声与振动控制,2014,34(4):205-208.
(CAO Bi-feng,YI Chuan-bao.Dynamic response analysis of wind turbine towers under wind and earthquake combined loadings [J].Noise and Vibration Contral,2014,34(4):205-208.)
[8] 何玉林,王磊,杜静,等.地震作用下的风电机组振动仿真分析 [J].太阳能学报,2012,33(2):179-184.
(HE Yu-lin,WANG Lei,DU Jing,et al.Vibration simulation analysis of wind turbine under seismic load [J].Acta Energiae Solaris Sinica,2012,33(2):179-184.)
[9] Domenico L,Subhamoy B,David M W.Dynamic analysis of wind turbines including soil-structure inter-action [J].Soil Dynamics and Earthquake Engineering,2013,49:165-180.
[10] 李德源,莫文威,严修红,等.基于多体模型的水平轴风力机气弹耦合分析 [J].机械工程学报,2014,50(12):140-150.
(LI De-yuan,MO Wen-wei,YAN Xiu-hong,et al.Aeroelastic analysis of horizontal axis wind turbine based on multi-body model [J].Journa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2014,50(12):140-150.)
[11] 李德源,池志强,汪显能,等.10 MW风力机叶片设计与动力特性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2016,38(3):241-246.
(LI De-yuan,CHI Zhi-qiang,WANG Xian-neng,et al.Design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blade of 10 MW wind turbine [J].Journal of 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016,38(3):241-246.)